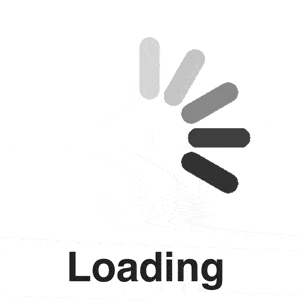我家的老屋(十)|作者:贺凤忠
半个月后,我拿着叔叔写的信在公社的农机厂门口截住了下乡回来的赵书记,在他的办公室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,让我去找高中的吴校长,他把我安排到了十二班。
一年的田里劳作,我又回到了学校课堂,这时已经开学一个月了,人虽然坐到了教室,但心似乎还有点散。文革中的一九七三年,有一个智育回潮现象,除了历史、地理、生物其它的课程能比较正规的进行课堂教学了,老师也大都是具有本专科学历。我比较喜欢语文和政治,但语文老师讲的课我不太喜欢,他说话太没有激情了,慢条斯理,高尔基的《海燕》一课,我们是怀着一个激动的心情,想听到他那绘声绘色带有丰富情感的描述,可是都在他慢条斯理中消失了!不过我写的作文,他还倒是在班上给以了几次肯定的点评!学过鲁迅的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》后,我有点改变了对李老师的看法,抽丝剥茧,层层递进,逻辑性的分析、判断,慢条斯理可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消化。吴校长的政治课,讲的非常的生动,一个个活脱脱的生活例子摆在你面前,一层层的理性分析,抑扬顿挫、铿锵有力的豫东腔调,我都不敢眨眼的注目着,黑板上一个圈接一个圈的把重点告诉我们,吴校长也是我叔叔的老师,他还记得当年我叔叔的样子。数学老师和化学老师是一对年轻夫妻,女的教我们数学,男的教化学,浓重的信阳方言听起来很费劲,后来知识分子归队,他们到县里的农机厂去了。数学老师的牌子最硬,北京大学毕业的,化学老师是文革前大学生。
我们家离学校有十里路,去上学之前,父亲就明确告知,没有自行车,走路,中午在学校吃一顿饭,早去晚归。拿家里的面在学校食堂换成饭票,中午的时候大部分是一碗汤面条一毛钱,再加一个馒头二分钱,偶尔吃上一次豆腐打卤的捞面条两毛钱,感到很满足了!冬天,母亲说太冷了,晚上住校吧?我们班寝室里大都是清华公社几个村的,原马营的砖井,会拉二胡。小中里的刘雨和,和我是同桌的。大中里的薛祖国,他家最有钱,父亲是村里的支书,吃的穿的和我们都不一样。倒槐树的郜喜胜,义沟的郝绍旺、郝绍材。早晚饭就是一碗玉米糊,就上自己带的咸菜再买一个玉米面膜,吃的也挺香,这是我有生以来的集体生活,感到快活!
村里和我一起在上学的还有几个,经常结伴往返的有大街西头的高恒,还有后街的陈三。高恒老家是北山上的,他父亲开小货点落户到我们村。从家到学校有时我们走的很快,比着走,有时又走的很慢,说着、打着、闹着,我记得一次在柏油路上两个人还练摔跤呢!
陈三在后街西头住,和他一起上学,走的是以前的老路,从他家的后门出来一直向北,穿过苏家作与怀村之间,过幸福河大桥再穿过汤庙南大街就到了学校。陈三和我是一个班的,我俩从小学开始一直就是同班同学,他很聪明,有读书的天分。上学的路上话题很多,一次聊起了卫生院,我说:“卫生院吧,要说应是最卫生的地方,但也是最不卫生的地方,怎么说哪?各种病人都要来看病,病人的身上的病菌就带到了医院,所以我不喜欢卫生院!”郜恒指着我,“你这是荒谬,卫生院是最讲卫生的地方,你看那医生、护士,白净的大褂一穿,多干净!给病人打个针,量一量、听一听,开个方,多有意思!”我俩争执的面红耳赤、不相上下。陈三说,“卫生院是给病人看病的地方,看好了就把他身上的病菌去掉了,”恢复高考后陈三考上了医专,数年后成了平顶山一家医院的院长,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!
在汤庙高中一年多的时间,我结识了同班的杨和平和候在富,我们成了好朋友,经常在一起谈论学习,谈论人生,也谈论社会。和平他家离学校很近,这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家庭,很穷,我们有时去帮助他家干活。在我后来的高考之路上,这位挚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,至今都难以忘怀!不幸的是,几年前因身患癌症,英年早逝!
瓦窑坑,是幸福河流经的的地方,汇聚了大量的河水,是一个天然的游泳池,炎炎夏日,很多人都到那里游泳,我和郜恒去了几次,终因胆小,我只下了几次水,郜恒硬是自己摸索学会了狗刨式游泳。公社里边有个大殿,那是解放后大庙拆除后唯一剩下的,夏天非常的阴凉,里边还有一个乒乓球台,班里的同学中午吃过饭经常在那打球、凉快!
几乎在每天的下午放学后,都能见到一个中年男子牵着一个男孩在幸福河边散步,这一个场景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还不断地闪现,那是学校的语文老师王佑桐和他的幼子小石头,王老师在县里的语文教学享有盛名,他不教我们班,在学校的大会议室里,我慕名聆听了他讲的《一封信》,那么多人,鸦雀无声,几十个字,他讲了一个小时!
学生们中间在传说着他的故事,王老师原来是一中的语文老师,妻子在炮伞厂上班,两人恩恩爱爱,经营者这个小家,小石头刚满一岁,炮伞厂发生一次大爆炸,小石头的娘不幸遇难,从此他是又当爹又当妈,害怕小石头受后妈的气,拒绝了别人的多次介绍,王老师受一起政治案件的影响,在农场学习一年后,到了我们学校。我们在学校总爱逗小石头玩。不知怎么,看到小石头总是想起红岩里的小萝卜头。
星期天的晚上我又到了石岩的小屋,他和玉秀已经约会了几次,他们两个商量要把事情告诉双方的父母,我俩分析了一下,担心的还是玉秀的爹妈,一个人家是城里人,能不能在这长期住下还不好说,再就是石岩她妈和他们吵过架,这矛盾能不能缓解也不好说。等一等,瞅个合适的时机再说,别一下搞砸了。
海棠生了,双胞胎、一对小男孩。王氏忙的跑前跑后,合不住嘴的乐。第三天,海棠的哥嫂送了鸡蛋、奶粉,还扯了许多尿布,交代了王氏,要把海棠伺候好,不要落下月子病,蓝天被获批了两天假,紧围着海棠,寸步不离,怕她受一点委屈。
村里的瓦窑第一窑砖出窑了,看着蓝灰色的青砖、青瓦,父亲的心里特别的高兴,中午还专门弄了一瓶焦作大曲和徐师傅喝了一顿,一块砖四分钱,一千块砖四十块钱,一窑五千块那就是二百块钱哪,徐师傅和我父亲是同龄人,从小就学烧窑,对火候的把握那是十分的精到。他性格豪爽,做事麻利,从不拖泥带水。和我父亲十分聊得来,他的妻儿老小在老家商丘的一个小荒村,食不果腹,寒无遮衣,生活条件极其困难,自己在这挣得几个钱大部分还得交回队里。他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太好了,羡慕我们的生活。
怀川像个牛角镶嵌在太行与黄河之间,是华北平原的最南端,属于太行山南麓的黄河冲积平原,土壤肥沃、旱涝保收,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,辛劳耕作,能自食自足,不用像京广线以东的农家,冬春还得去讨饭。这里的住房虽不全是浑砖,但几乎没有草房,都是青瓦盖顶,青砖根基,好一点的家户,门窗也都是青砖封围。南方的粉墙黛瓦建筑特色在这里有所体现。
父亲邀请徐师傅来我们家做客,家里的摆设,爷爷的做派,徐师傅连连称赞,你们家是大户人家呀,我们那里以前的大地主才会是这样的家,你们也是文化人呀,这中堂上的字,多有气派。这一顿饭徐师傅是没实打实的吃,有点拘谨。
梅花的姑又来了,小伟在部队立了个三等功,郊区武装部敲锣打鼓把立功喜报送到了家,小伟的家人想尽快把两个人的婚事定了,选了个日子,换手巾。今天梅花她姑就是为这事而来。
前些时候,梅花他爹有点动摇,可是赵克礼对他提出的事一点都没放在心上,心中就没有他,那梅花和他那个事就彻底算了。
元旦,小伟探家,两家定的就是这天换手巾。梅花知道这个消息是她爹通知他的,不是和她商量的,没有任何余地,梅花两天没有吃饭,她爹也两天没吃饭,家里人急的不知该劝誰?梅花知道爹的倔劲有多大,自己绝不是对手,可自己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,自己喜欢的人自己不能嫁,实在是不甘心!梅花偷偷写了个纸条塞到弟弟手里,嘱咐他给赵克礼送去。
赵克礼正在大队部筹划着成立大队副业队,榨油房、轧花房、面粉加工厂、预制板厂、砖瓦窑都陆续的建起来了,管理要跟上去,才能见实效。他在想着副业队的队长的合适人选,于和平,年轻有活力、激情,处理事情很有章法,是一个合适人选。梅花的弟弟匆匆而来交给他一个纸条,转身就走了,看完纸条他的脸色凝重,思考了半天,梅花非常可爱,可是他的父亲咋这么封建?新社会已经二十多年了,为什么婚姻还不能自由哪?自己目前这个处境,这个事又不能闹得太大,得顾及一些影响啊!唉,说到底,这个事主要还是决定于梅花本人了。不过自己绝不能隔岸观火呀!
赵克礼又去找了冉大志,想让他去劝劝梅花他爹,冉大志面露难色,“克礼,这个事难办呀,我哥那个倔劲动了,谁也劝不回来。”“那,你说怎么办?”“这主要看梅花了,不过,我再给你说说吧!”
冉大志还是没说动梅花他爹,元旦换手巾一天都没改。梅花他爹认定了赵克礼不会给梅花一个好过的日子,认定了小伟这个孩子将来才是有大出息的,梅花跟着他能奔着个好日子,家里也能沾点光。
海棠的一对男宝宝可是累坏了她的婆婆王氏,海棠看在眼里心里是感激万分,有苗不愁长,一天一个样,快满月了,海棠和婆婆商量办满月酒的事。婆婆有点担心,“海棠,咱们这个家庭,你说能办的起来吗?”“咋办不起来?村里家家不都是这样办吗?再说了,我家那头满月时还都要来哩!”“是呀,你家哥嫂、亲戚朋友还都要来,那咱们就准备几桌。”
七四年的春夏之交,又一场风波开始了,学校里发生了一起案子,大会议室的黑板上几个白色粉笔字引起了人们的警觉,大会议室平时就没有关过门,经常有学生进进出出,中午休息,下课课间时就没断过人,也经常有学生在讲台的黑板上胡乱涂鸦,不时地写了涂,涂了写,谁也没在意,忽然有一天黑板上有这么几个字串到一起了,越看越吓人!县公安局进了学校,弄了一阵子,什么结果也没有。有人说那本身就是一场闹剧,不相干的文字在胡乱涂抹后的偶遇。
又过了一阵子“不学ABC照样能种地”、“高考交白卷“等事情接二连三冒出来了,学校也传达了上边关于“智育回潮的”的文件,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了,上课时间,不少的学生在汤庙的街上闲逛!
蓝天又请了两天假给孩子办满月,拉了个平车去城里赶了一个集,请了两个厨师,找了几个帮手,准备了八桌酒菜,大队、小队干部都通知了,还有几个要好的。
接近中午的时候,海棠的哥嫂领着一班他家的亲戚、朋友进了门,海山、海洋、海云都赶快迎接。已是中午,蓝天和海棠两家人也只坐了三桌,还有五桌全是空的。蓝天有点失落,可还是满脸高兴,海棠脸上可是挂不住了,愁云密布。
工作组又进村了,组长已经找过我父亲谈过话,没有一点恶意,只是想把我父亲这个右派身份问题能清楚,让他能放下包袱轻松干事。
农村的人是靠公分吃饭的,队里的公分值很低,每个劳动日两毛多钱,家里七、八口人就依赖父母亲两个人,我虽然一个月只需两三块的伙食费,但家中也无力承担。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,爷爷把我叫到堂屋的桌前,“小桐,你现在也不小了,你看家里现在这样,你还能再上学吗?你该为你爸分挑点担子了!”
爷爷最后的话打动了我,是的,父亲是内外交困、身心疲惫呀!几年前的一次病发,使我更加警醒!那时他是生产队的副队长,在敲响了井台旁边钟声后,突然倒在了井台旁,准备上工的邻居们掐着他的人中把他从昏迷中唤醒,医生来看了说是劳累过度,我当时只是默默地站在他的床头,连一声爸爸也叫不出来!无需再多想,我对爷爷说,那我就不上了!
七四年的冬季来临了,县里为了深入学大寨,在北石河的乱石滩上造田,全县各村主要劳力都云集北石河附近。那个年代每个冬天都要干一个工程,每个工程都是农民身上的血汗。
高中学生停课一星期,自带工具和干粮去北石河参加劳动!我没有去,我不上了。
没几天,我就被队里派到石河造田工地了。石河的东岸是焦作市的郊区,附近有一个空廓的粮站,各生产队就在此宿营造饭,不管平时在家里怎么俭省,工地的伙食还是不错的,炸酱面、炸油条,油壮馍变着法让大家吃好,我顺便还带了一个笛子,晚饭后还吹上一曲,不觉得累,两三个人一个小平车,把从坚硬的黄土断崖上刨下的土铺到那乱石滩上。村里的青年男女大部分都去了,石岩、茅桶,玉秀都在其中,拉车的,装车的可热闹了,我们队分得了有五米宽、四十米长,估计的一个月才能完成。一场大雪,人们都从工地上撤回了家。
元旦来临了,梅花要和小伟换手巾了,她穷尽了脑子也没有办法改变她爹的主意,不要命的威胁使她别无选择,只能屈从。
赵克礼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,他在反复的思考着,农村、农民,这个黄土地,可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个简单,封建、封闭、落后的守旧思想、势力,在各方面阻扰着前进的步伐,拨开它,不是容易的事!
我已经不上学了,可在这块黄土地上干下去,不是我的打算,我的周围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都进了城,当起了工人,关系强的被招进了厂,是正式工,关系差一点弄个合同工,再差的先干个临时工,一个月几十块钱,抵得上在家干一年的活。劳动服那时最时髦。后街王石磙他儿,春节穿了一身劳动服工作衣,把全村的年轻人羡慕的不得了。
家乡的黄土是百里怀川最粘的,它能粘的你拔不出脚而深陷于此,我们的人生不能就陷在这片黄土里,不敢说眼光有多么的遥远,志向有多么的大,可冥冥能感受到更光明的地方就在那天边不远处,如何摆脱困境,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新天地!有多少个夜晚在石岩的小西屋,我们都在苦苦的思索,一定要走出去!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念!
我和石岩的叔叔都在焦作上班,我们寄希望于他们。每个月叔叔要回老家看望爷爷和奶奶,会带了一些消息,快到他回来的那几天,我的眼总是在盯着马路边。
紧张的三秋工作又要开始了,工作队又和我父亲谈了一次话,争取尽快的澄清他的右派身份问题,为下一步工作安排做准备,工作队还是希望我父亲能挑起我们这个队的队长职务。
工作队和赵克礼商量后,请示了公社,明天由于和平和一名工作队员先到县组织部开介绍信,然后奔赴温县去详细调查。同时也告诉了我父亲。
去温县调查,就注定了父亲这个隐藏多年的右派身份要暴露出来了,父亲就要挨批斗了,家门口要挂上右派分子的黑牌子了,我们从此就抬不起头来了。这是父亲、母亲和我一夜未眠而反复萦绕在脑子里的事,当然也盼着在这冥冥之中能有一线希望!
我家祖坟上有一棵老柳树,那是多年前曾祖父下葬后,在坟前插的柳幡,枝繁叶茂,荫护着整个坟地。
于和平他们回来了,没有去温县,县委组织部的干部都下乡帮助三秋工作了,开不了介绍信。
危机暂时解除了,可母亲的精神一直不好,晚上经常做噩梦。
转眼就到了秋末,队长到家里来,带着一番好意的说,“大队给咱分了一个指标,去北石河整理造出的田地,俢渠垒坝,干好了最后还能留到那里的!”我是铁了心的要离开这黄土地,叔叔也传来消息,正在托人找,父亲找理由推脱了队长的安排。
冬天到了,几年一轮的沁河修堤工程开始了,车辚辚,马萧萧,农民们又出征了!队长通知我上大堤工地,住宿在张武村,工地在南张茹,太远了!刚住了一晚上,就搬到了武阁寨。
我没有和队里的人住到一起,我住到了石岩他们队的宿舍,那双圈挺能讲笑话,还有疙瘩也挺能逗人的,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。
修堤,就是挖河滩的土用小平车拉到几十米高的大堤上,再用拖拉机碾平压实,把堤修高。有条件的大队,用柴油机把一车车的土绞到上边来,我们村是靠人拉的,三个人一辆小平车,每个人都是用尽浑身力气才能把一车土拉上来,我和轱辘、满圈一辆车,那么冷的天,里边的衣服都湿透了。我的大堂哥是负责修路的,不时地替换我一下。我长这么大,这是出力最大的活,我记得那时脚上穿的是一双解放鞋,先是脚后跟露出来了,再是破了、冻了,也不知道痛。
第四天中午吃过饭,我坐在大队伙房旁的一块青石上,透过一侧的月亮门,看着外边那一簇青竹。
石岩和玉秀从月亮门走了进来,他俩刚从大堤上下来,石岩是大队工地指挥长,这是王克礼有意培养,亲自点的将,他俩又去说悄悄话了。石岩给我招了一下手,我起身过去,他低低的说了一句,“你爸让你回家哩!”我知道叔叔给我找好了临时工。
半夜时分,我手捂着肚子,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,疙瘩起身跑到我们队里的宿舍喊队长,队长没来,捎来一句话,“让他忍着吧,天明找医生!”我折腾了半夜。
早上,在伙房当炊事员的二伯和村里工地的医生一同走了进来,二伯端了一碗饭让我吃,我还是手捂着肚子,痛苦的摇摇头,不吃!医生按了按我的肚子,问我哪里疼?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包,抽出几根长长的银针,我有点害怕,前年,我拉着平车送爷爷去苏家作老争光那扎针时,见过比这还长的针。医生在我的肚脐周围扎了几针后,我还是一副难忍的疼状,医生说,怕是阑尾炎,赶快回家去医院吧!
我回到了家,叔叔找到了临时工,但是在那个年代,农村里的人是不能随便出走的,我的本家哥,早年修铁路,留在了工地,可户口没走,几年后硬是让大队给要了回来,石岩的三叔在县里土产门市部干了五六年也是户口没走,刚刚被大队要了回来。出去外边,必须有大队出具的证明,怎么办?我想到了前几年赵克礼在传达9.13事件的文件时,有借助钟馗来打鬼,既然鬼怕钟馗,那就找一“钟馗”吧!
那是快到冬至的一天的早上,嗖嗖的小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庞,碎棉絮似的雪花在空中尽情的挥舞着,我急匆匆的走在去往后街的路上,赵克礼去县里学习了,程三又临时负责两委工作,他住在后街,我推开他家的大门,他媳妇正在打扫院地,“麦青姐,我三哥在吗?”麦青的父亲打小和我父亲是好友,“在!还没起来。”“程三......前街明楷叔家的小桐找你!”她朝着屋里喊道。“你进去找他吧!”麦青推开了屋门,我走进了屋里,铁锁光着上身从被窝里坐起,穿上了压在被子上的军用棉袄,“啥事?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他,说:“三哥,这是公社赵书记给你写的。”他看了纸条,说:“您家还有这硬关系。他拉开了床头桌子的抽屉,拿出大队的公笺、公章、印台,给我开了个证明。回到家后,父母亲松下了一口气,他们很担心我。
作者简介:贺凤忠,笔名丹水岸边,河南焦作人,出生于1958年11月。童年经历了三年灾害的饥荒年代,求学于动乱的十年文革,当过农民,干过矿工,恢复高考后,考入大学学习,毕业参加工作后,先在农业战线工作,后一直在中学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至退休。
责编|王芳编辑|玉川子图片|网络
标签: 梅花 父亲 大队 海棠 队长 工地 石岩 叔叔 语文 卫生院
声明:本文内容来源自网络,文字、图片等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,平台转载素材出于传递更多信息,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与学习,切勿作为商业目的使用。如果侵害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您及时与我们联系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!我们尊重版权,也致力于保护版权,站搜网感谢您的分享!